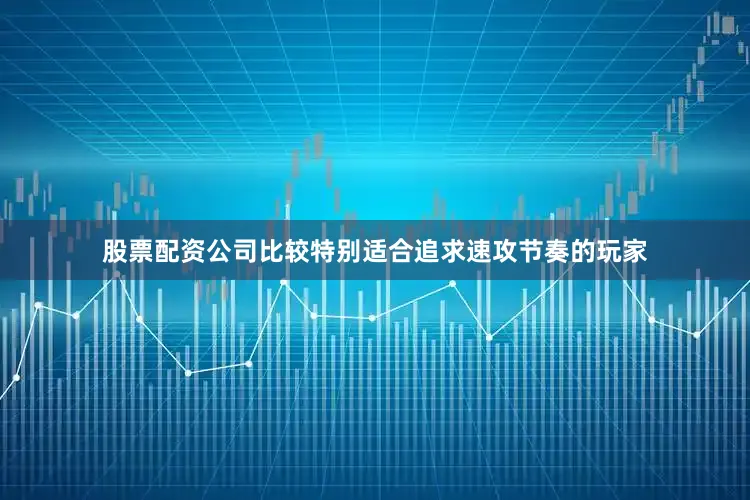在洛阳与西安的历史争夺中,洛阳由于建都次数的短缺,便从众多史料的边缘中寻找任何蛛丝马迹,无论其合不合逻辑,甚至不管这些内容是否有实质依据,只要能支持自己的论调,就毫不犹豫地拿来作为证据。在网络上,尤其是百度百科的《洛阳》、《雒邑》、《成周》等词条上,他们对这些历史内容进行了疯狂篡改,力图塑造一个与西安相抗衡的历史地位。为了达成这一目标,洛阳方面主要依赖以下几个不够严谨的证据。
一、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的断章取义
洛阳方面引用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所说的“昔三代之居皆在河、洛之间”,断言夏、商、周三代的都城都位于洛阳。然而,这种解读忽略了后文的重要内容,断章取义的手法使得这一论证显得非常薄弱。事实上,接下来的文字进一步解释了“河、洛之间”的涵义,原文提到:“……故嵩高为中岳,而四岳各如其方,四渎咸在山东。至秦称帝,都咸阳,则五岳、四渎皆并在东方。”如果仔细阅读整段文字,可以清楚地知道,所谓的“河、洛之间”并非指的洛阳的那一段黄河和洛河,而是泛指整个黄河流域,甚至包括陕西、河南等大片地区,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围。
展开剩余77%更重要的是,《史记·封禅书》并非针对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王朝历程,它属于一篇《封禅》的纪实,属于记载诸侯国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。相较之下,三代的历史正史《帝王本纪》更具权威性。当时的帝王本纪并没有直接表明洛阳作为都城的地位,尤其是在《周本纪》中,西周的都城被明确记载为丰镐,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洛阳曾是京师。
二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混淆与错误解读
另外,洛阳的支持者还引用了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对雒邑的描述:“昔周公营雒邑,以为在于土中,诸侯蕃屏四方,故立京师”,并据此推论出雒邑就是西周的京师。然而,这一论断同样是断章取义,且存在明显的历史矛盾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的描述,实际发生在东汉时期,距西周时期已相隔几百年。东汉的班固显然无法直接了解西周具体的历史细节,尤其是西周的周公并未在其时期定都雒邑。
事实上,班固所言“故立京师”后,紧接着的内容又提到:“至幽王淫褒姒,以灭宗周,子平王东居雒邑。其后五伯更帅诸侯以尊周室。”这段话存在明显前后矛盾的地方。若真如班固所说,周成王定都雒邑,那么为何后来的周平王迁都后,才有了“东居雒邑”的说法?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,且与《尚书·雒诰》的记载相违背,表明此处的“立京师”应该是误记或后人的篡改。
三、《吕氏春秋》的误读与夸大
接下来,洛阳支持者又拿出《吕氏春秋》中南宫括的言论:“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?”来证明周成王曾定都成周。然而,这个证据虽然没有完全断章取义,但它仍然对历史的理解产生了错误解读。首先,虽然《吕氏春秋》确实成书于战国末期,但其作者吕不韦的用意是教导嬴政如何治理国家,而并非追求历史的严谨性。《吕氏春秋》中的南宫括所言,也许是道听途说,并未有确凿证据证明周成王曾经将成周定为京师。
根据《尚书》的记载,周成王确实在五年时曾短暂驻留于成周,但他并未将其定为京师。周成王之所以停留在成周,仅是出席雒邑的建设和庆典活动,这与定都一事相去甚远。因此,洛阳方面引用这一材料来证明成王迁都成周,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读,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撑。
四、《何尊》铭文与篡改
另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《何尊》铭文,洛阳方面试图通过“惟王初迁,宅玆成周”来证明周成王曾迁都至雒邑。对于这一说法,我在前期的研究中已有详细论证,周成王并未迁都。铭文中的内容并不如洛阳方面所解读的那样直接证实这一历史事件,甚至可以说这种解读带有强烈的主观偏向。
五、篡改文献与铭文的虚构
洛阳支持者还通过各种手段,断章取义、误解、甚至篡改史料和铭文,来为自己塑造历史。例如,《何尊》铭文并未提到“王城”一词,但在河南的百科词条中,却故意加上了“王城”。更有甚者,在对西周首都的描述中,河南方面自行创造了一个“雒京”这一词汇,虽然在西周的任何文献中并未出现过这样的称谓。
西周的宗法分封制明确规定,周天子所居的宗周就是京师,而各诸侯国则有自己的“京”或“成”称谓,因此成周并非洛阳的京师。在西周的文献和青铜铭文中,并没有任何关于“雒京”或“王城”的记载。历史最真实的解答应来自最早的原始材料,而这些未经后人篡改的史料才最具权威性。
结论
总的来说,洛阳通过断章取义、误解和篡改历史资料,试图将洛阳抬高为西周的都城,但其历史证据站不住脚。真正的历史应以西周的官方文献和考古材料为准,而非后世的解读和主观臆测。
发布于:天津市富灯网配资-短线配资平台-配资网址-线下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按月配资开户(元/吨)
- 下一篇:无锡股票配资公司能折射出每个人不同的模样